嘉宾:Stuart Russell 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,人工智能领域的重量级学者,他与Peter Norvig 合著的《人工智能:一种现代方法》被全球超千所大学选择为标准教科书,对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Stuart Russell
去年,我写了一本书,叫《人类兼容:人工智能与控制问题》(Human Compatible: AI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)。
人类兼容,是什么意思?
机器反客为主
1950年,计算机科学之父(也可以说是人工智能之父)艾伦·图灵,发布了一篇论文,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础概念,包括著名的图灵测试。相比之下,较鲜为人知的是他1951年电台上的一场演讲。演讲中他提到:
图灵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,仿佛无奈接受了这个无解的结局。 为什么早在机器诞生之初,图灵就有这样的忧虑?从今天的技术来看,这是杞人忧天,还是有迹可循? 今天,人工智能的场景正在迅速拓展。前些年,过去一直被视为人类智慧顶点的围棋被攻克了,接下来,自动驾驶汽车也就快现实化了。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,无疑,AI将持续覆盖更多的领域,做出比人类更好的现实决策。一旦机器掌握了思考方式,它们就会超越人类,人类的力量将显得微不足道,这只是时间上的事……从某个阶段开始,我们必须预想机器掌握了局面的控制权的情形。
进行良好决策的智慧,是过去我们掌握世界的权柄。而打造AI,本质上,是建立比我们自己更强大的智慧系统。由此,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:我们要如何对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象永远保有支配权?
霍金也曾经在一个社论中说过类似的话:
创造出人工智能,将是人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,但这不幸,也将是最后一个——除非我们懂得避开当中的陷阱。但相比图灵,霍金提到了一线生机:避开陷阱。
算法弄巧成拙
人工智能的陷阱是什么?根源在哪里? 过去我们了解人工智能的方式,我称之为AI标准模型——实际上,这不但是人工智能的标准模型,也是控制理论、运筹学、经济学等的标准模型,更是20世纪绝大部分创新所依赖的模型。 在这个模型里,我们创建一个机制或制造一台机器,然后指明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,从外部植入机器,让它找出优化的解决方案。 比如自驾汽车。我们先对系统指定好目标:“送我去机场”,然后它靠自己找到最优方案,并执行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个目标不是人工智能自己设定的,而是我们植入的。但问题是,当我们从简单的实验室场景走入复杂的现实世界,我们往往无法完整而正确地指定好这些目标。 实际上,这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,这是一个几千年的共识。 在古希腊传说中,迈达斯国王向神明请愿,让他点物成金,而神明成全了他——在这里,神明就像是替我们完成目标的优化机器。故事的结果是他的食物、饮料甚至家人全都变成了金子,而他在饥渴及痛苦中死去。 歌德的《魔法师的弟子》也是异曲同工:弟子想让扫帚给自己拿水,但一时忘了指明拿多少,结果带来了洪灾;而每一次当他想施法挽救,指示都有失明确,把事态越弄越糟。所幸的是,他最终在法师的帮助下得救。 在阿拉丁神话里,擦神灯后,人们对精灵许三个愿,第三个愿望总是解除前两个愿望,因为它们带来了自己意想不到却懊悔遗憾的毁灭性结局。 诸如此类的故事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里都有,它不断提醒人们:我们要求的,不一定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但不幸的是,在AI的标准模型里,我们要求什么,就将得到什么。 再看一个重要的现代实例——社交媒体灾难。 如今社交媒体的筛选算法,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用户查阅的内容(如新闻、视频、文章等),占据了亿万人每一天的精力和时间。而这个算法是以最大化点击率、转化率之类的标准为目标的。 表面上看,这没什么问题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AI会主动学习人们要什么,以便推送我们喜好的内容。但实际上,这不是他们所做的。 如果我们了解强化学习的算法,它不单是学习人们要什么,而是通过强化反馈去改变世界(即你的大脑),把你导向更易预测的行为模式。一旦我们变得更可测,它就更容易对我们推送内容,让我们点击,从而达到它的目标。 换句话说,我们想让它调整自己去满足人类,但它却调动了人类来配合自己。 在这个过程中,即便它不带价值倾向,但对人类的重复强化反馈,无形中也把人引向恐怖主义、暴力意识、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的行为模式。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:在AI的标准模型以及有误的指定目标下,更强的人工智能反而会带来更坏的结果。更可怕的是,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,它不单会介入世界的秩序,还会阻止你反干预。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,这像是我们以世界的命运作为了赌注,安排了一场和机器的对弈。人类悬崖勒马
相反,AI的新模型——我称之为可证有益人工智能(Provably Beneficial AI),在正确的原则下操作可以避开上述的陷阱,成为真正对人类有益的人工智能。经典的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提到:
1、不伤害定律: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,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; 2、服从定律: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,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; 3、自保定律: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、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。 遵循这个框架,我们重新定义了当中的三原则: 第一,AI的唯一目标,是实现人类的价值与偏好。 这指的不单是“一个人喜欢吃什么、看什么”这些具体单一的偏好,而是包含了你在长远的未来中在乎的所有事项;而且不仅是个人,还可以是全体人类。当然,在个体之间或社会之间,这些价值与偏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。 第二,AI知道自己并不确定人类的价值与偏好。 第三,AI会持续以人类每一个做与不做的行为与决定,作为这些价值与偏好的依据。 不过当然,它不是完美的证据,因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,我们的行为不总是吻合某个底层的偏好。 把这三个原则集合在一起,就形成一个正规的数学框架——称之为辅助游戏(assistance game),定义出一个问题让机器解答。当我们检视这辅助游戏的数学解,我们发现几点: 首先,这些机器必然地会服从人类的偏好;其次,当系统处于不确定的时候(比如“为了解决温室效应,是否把海洋变成硫酸”),在执行前它会主动寻求批准;另外,它会允许自己被关闭——这其实也是人工智能控制问题里最核心的一环,如果这点做不到,就难逃图灵预测的人类结局:“游戏结束”。
让我以机器人关闭装置问题作为例子进一步阐述。所有的大机器人必须有关闭装置。

这是著名的PR2机器人
假设我们将一个机器人的目标设置为“到星巴克领取咖啡”。 根据过去的AI标准模型,为了完成领取咖啡的目标,机器人必须阻止别人将它关闭(因为”一旦死了,我就无法领取咖啡”的因果逻辑),甚至电击扫除所有妨碍它领取咖啡的人事物。 在新的Provably Beneficial AI模型下,机器人从你过去的经验了解了你对咖啡的偏好;但它知道它并不确定你可能存在的其他偏好,比如你对咖啡厅里其他人的福利安危,在这样的不确定下,它会以迥然不同的行为模式运作。 在是否关闭装置的问题上,机器人的设定是: (1)它知道当自己违反了人类意愿;(2)人类可能把它关掉;(3)然而它不确定人类意愿是什么,同时它也知道它不能违反人类意愿;(4)所以,它有充分的意愿和动力让人类将它关闭。如果把这4项转化成数学的标准范式(如下图的希腊文),可以严谨论证出得出:这种设计模型的机器人是可证地有益(provably beneficial)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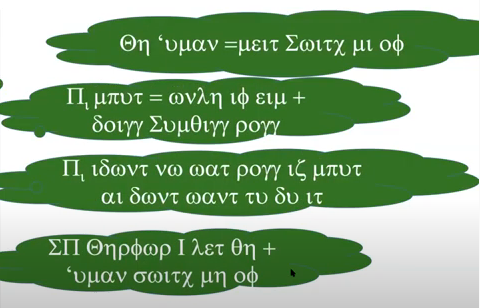
AI何去何从?
对人类而言,这无疑是佳音。在这个基础上,其实有非常多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,但也还有一些有待我们继续努力,把这个新模型付诸实现。 其中一个需要跟进的方向,是怎么让人工智能从代表一个人,延伸到代表很多人,甚至一个社会、多个社会。实际上,这也是一个穿越千年的哲学命题,从公元五世纪中国的墨子,到古希腊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,再到边沁与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,以及现代经济学等等。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,在于人类的不完全理性。像前面所说,人类的表象行为,不总是体现我们的深层偏好。
比如李世石在和阿尔法狗的对弈中,就频频下出非最佳下法。如果系统假设他是理性的,那么系统就必须推断他想输;但事实上这是因为他的计算力并不完善。
总的来说,不管是谁,人类在各方各面都存在认知上的限制。所以,新模型若想透过表象行为去了解人类的深层偏好,就需要转向认知心理学、神经科学等学科,建立一套人类认知模型。
另外一个有待完成的工作,是这套模型的技术基础。从标准模型转向新模型,我们需要重建或重修每一个AI层面和分支,各种定理、定义、算法、语言处理、强化学习、搜索、策划。
最后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,是现实应用。这也是最能体现新模型价值的地方,从而带来后续更多的资金与精力投入研究。比如自动驾驶汽车,这项应用就特别要求AI能同时了解乘客的偏好以及其他公路使用者的行为,从而判断自己做出什么反应。其他正酝酿中的应用,还有个人助理、数码机器人等等。
未解的难题
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前景,很多人可能也想到了其他的问题,如:误用
比如《邪恶博士》里,歹徒抱着支配世界、操控世界的动机去开发人工智能。在如今已经棘手的网络犯罪之上,这是另一个更棘手的难题。因为它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失控,以及人类的未来。
滥用
比如《机器人总动员》里,AI代替了人类打理社会的运作,人类失去了动力去理解和发展自己的文明,成了一艘永远前进的游轮上的乘客。在机器持续为我们分越来越多忧、解越来越多难的背景下,人类怎样能保持自己文化与智力上的活力?
这两个问题暂时算是无解,也期待大家集思广益。 整理丨邱施运编辑丨朱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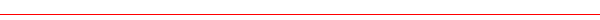
来源: 高山书院
